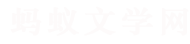《银河街十日谈》 Day5 免费试读
『那人目眦尽裂,手里刀刃一翻,即刻在齐知礼脖子上划出一道血痕。』1941年12月5日凌晨 0点30分
上海北站。
火车在松江出了点故障,晚点一个半小时。本来夜里十一点出头能到的列车,硬是拖到凌晨。
江雁宁从火车上下来,站到这熟悉的地方,才想起一天前自己上车的缘由是被日本人追啊!我的天!想到这里她简直要冒出冷汗来。两只脚犹犹豫豫不肯往前迈。
齐知礼拍了拍她肩膀,很快把手收回去:“放松点,这么晚了,应该不会有人等你这个没什么价值的学生的。而且——你现在是个留学生了。”夜色中,他甚至挑了一下眉。
江雁宁一愣,她这才反应过来——齐知礼之所以带自己去买衣服,全都是因为这一刻。这个认知超越蜜饯带来的酸甜感,全然是一种由衷的感动。
她甚至没有在意,齐知礼揶揄她“没什么价值”。
齐知礼伸出胳膊,示意她挽住,两人用一种得体得近乎夸张的步伐走出火车站。
黑色福特车上,齐知礼说:“你还真把电影里的留学生学得入木三分啊。”
江雁宁得意洋洋:“那当然!我可是认认真真看的。”
齐知礼看这她笑眯眯的傻样,愣是把那句“但她们没有你夸张”咽了下去,“送你回去,住哪?”
说起这个江雁宁不高兴了:“你不是知道吗,还要找人来帮我们搬家呢!”
然而齐知礼何尝不心累呢,谭为鸣这事不知道办得怎么样了,杭州出发前也没打个电话问他,但此刻也不用想了,等回头见了面再说。眼下得先送江雁宁回去:“我是问你,你在上海住哪。”
“我等着住寝室啊,也不知道汪老师有没有帮我安排好了。”
齐知礼几乎崩溃:“没有寝室的时候你是住哪的?”
“爱多亚路亭子间呀。”
“那我送你回去。”
“不不不。”江雁宁拦住他,“房子快到期了……当然也、也不是不能再住一两天。但是……”她扭扭捏捏的。
“但是什么?”
江雁宁心一横:“但是都这么晚了,我回去要是被邻舍发现,谁知道他们得怎么编排我啊。亭子间不隔音,邻舍间从来没有秘密的,这你也知道——哦对,你不知道的,你没住过。”
齐知礼默不作声看着她。
江雁宁有点尴尬,觉得自己一定已经变成了齐知礼的***烦,是以马上说:“没关系,你现在就回去睡觉,车停在门口让我躺一躺就好,我六点半还要起来去上课。”
齐知礼点点头:“也可以。那你就睡在我家院子里,顺便帮忙看门吧。”
“好。”江雁宁点完头又觉得不对,“你是不是在骂我?”
齐知礼一本正经:“没有啊。”
“你说我是狗!”江雁宁举着手控诉他,“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齐知礼忍笑功全破了,连声说“哪有哪有”,又讲,“看来是不肯睡在院子里了。”他停了车,招呼江雁宁,“下来吧。”
江雁宁抬头一看,是锦江饭店:“算了吧,没几个小时天就亮了,睡在这里怪浪费的。”
“这儿是我家招呼客人的长租房,钱早付过了,不睡白不睡。”齐知礼去服务员那里拿了钥匙,带江雁宁上楼。
与新泰饭店的雅致相比,这里要洋气得多,床啊柜子啊,样样都花纹繁复,据说是欧式的风格。
齐知礼替她进盥洗室调节水温:“洗澡的话里面水温正好,我先走了,你早点睡。”
江雁宁站在光芒四射的水晶灯下,脸上现出一点少见的扭捏,“哎”一声叫住齐知礼。
不知是不是错觉,齐知礼觉得她似乎有点脸红,高亮度的灯光照在江雁宁身上,齐知礼甚至能清晰地看见她脸上细白的绒毛,她仍然穿着那件米白的开司米大衣,像一只毛茸茸的小兔子,仿佛是柔软脆弱的,却又随时可能拔腿狂奔或张口咬人。齐知礼想到这里忽然“嗤”一声笑出来,这一笑,心里忽然极细地颤了一下。
他盯着江雁宁,说:“是不是要我给你讲睡前故事。”
江雁宁连忙摆手:“是这样……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那天那么急赶到杭州,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忙吗?”
齐知礼吸了一口气,心中涌过一阵酸涩的暖流,他伸手拍了拍江雁宁的肩:“会解决的,别担心。”拍完忽然觉察出不妥来,僵了一下收回手。
江雁宁把手从大衣口袋里伸出来,右手掌心朝上,对着齐知礼托出一个东西,“我去灵隐寺求来的如意符,希望你能顺顺利利解决麻烦。”
齐知礼出现了一瞬短暂的、自己没有预料到的沉默,他站在江雁宁对面,抿了一下嘴唇,想说点什么,却发现无从开口。
江雁宁笑起来,大眼睛弯成月牙,拉起齐知礼的手腕,把东西塞进他手里:“干嘛,感动啊?”
齐知礼握着那个如意符,手紧了紧,忽然笑起来:“你别是本来想留给自己,现在睡了我家客房觉得不好意思才拿出来给我的吧?”
“我不好意思个屁!你才要不好意思吧。毕竟想赶走我们整条街。”江雁宁脸上的笑褪去了。
齐知礼一时无言以对,气氛尴尬到两人都别开了视线。
半晌,齐知礼干咳了一声,讪讪地说:“你早点休息吧,我走了。”他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来,看着仍然立在原地的江雁宁,露出笑容来:“谢谢。”
江雁宁留在屋里,看着齐知礼掩上门离开,想起自己提起银河街时,他那焦虑却无可奈何的神情,忽然想:会不会他的烦恼其实和银河街有关?想到这里,她忽然有点不必要的自责了:嗐!好好的晚上,提银河街做啥……
齐知礼下楼去结账。什么长租房,我齐家那么大个别墅,招呼人还要租饭店客房?嘁。他回到车里,借着饭店门口些微的灯光细细看那如意符,心里忽然被一种名为“动容”的东西裹挟,他想起在去往杭州的火车上江雁宁还吃了个牛肉三明治,昨日却是死活不肯吃荤菜了——原来都是为了在自己手里的这样东西。
是夜,月黑风高,齐知礼却觉胜过繁星漫天。
1941年12月5日上午 11点05分
银河街,江家。
董心兰端上百叶结烧肉,边用围裙擦手边笑:“老沈你尝尝,我买了最好的五花肉。”
老沈喝酒有些上脸,一碗绍兴黄酒下去面色已经泛红:“阿嫂你快别忙了,坐下一起吃。”
“我再去炒个青菜。”
“别忙了,你看这……”老沈指着桌上的狮子头、蟹粉豆腐和鱼汤,“这些都吃不了了。”
江志高挥了挥手,示意他吃菜:“知道你最爱吃‘赚头’,你嫂子特地让我去‘陈卤记’买的。”“舌”和“蚀”发音相同,所以‘猪舌头’要说‘猪赚头’。
江家这样客气,老沈当然知道是为了啥事。自己的姑父在军队里做师长,下头大大小小的事说话都有七八分分量,本来凤平吃处分也不是啥太大的事情,虽然凤平不在自己姑父手下,但难道他去说个情,人家还能不买面子不成?结果呢,偏偏凤平他们那新来了个参谋长,脾气又臭又硬,像块茅坑里的石头似的。什么?你说他们那师长吃不消参谋长?那哪能!关键这参谋长的爹和上头亲近着呢,人家犯不着为了一个江凤平得罪他。
老沈喝着酒把这事嘟嘟哝哝地说了一遍,董心兰听不下去了:“我们凤平也不是混日子的兵油子,年头上不还立了功嘛!怎么为了救人晚了点时间就要处分,这也没误事啊!”
“不是这么说的阿嫂,当兵第一就是要服从,凤平这属于不服从。”
董心兰瞪了他一眼,本来还想辩驳,念及这事恐怕还要托他,愣是把话咽了下去,好声好气说:“老沈,你也是知道的,凤平一心想驱除日寇报效国家,几年来也是扑心扑命,前阵子还说要升上士呢,这一下给降成个上等兵,哪能受得了啊!”
老沈这饭都吃了,还收了点礼,手短嘴软:“阿嫂,你呀,我跟你说,我都替你问了,你知道那参谋长是谁!”
“谁?”
“你们这银河街谁盖的?”
“齐老太爷呀。”
老沈咂一口黄酒:“那参谋长啊……就是他孙子!”
话一出口,江家夫妻俩都吓一跳,对视了一眼,心上都浮起齐知礼那高瘦的模样。江志高忍不住说:“那小少爷年纪也太轻了点儿吧,人也不像能打仗的样子啊!”
老沈愣了一下:“你说的是来收银河街那个吧?那是他小孙子。当参谋长那个是大孙子,叫啥齐知……知廉!他爹就是那大名鼎鼎的齐树人……”
董心兰不由问:“那和上回来收银河街的小少爷是嫡叔伯兄弟了?”
“是呀!齐老太爷就两个儿子,大儿子齐树人,生了个参谋长儿子,小女儿好像送到外国去了;小儿子齐树新,有个管生意的女儿和一个据说刚大学毕业的儿子。齐树人如今和委员长都攀上关系了,哪还有兴趣管生意,齐老太爷留下来产业我看都是他小儿子在管了。哦唷,想想有钱人家多少开心,家里留下那么多钱真是一辈子不愁吃穿了,我们老百姓呢,混口饭吃还要做生做死。”
董心兰听到这里一拍大腿:“哎哟!你看我,炒青菜都忘记了。”
1941年12月5日上午 11点10分
锦江饭店。
江雁宁醒转过来,眯眼回忆了一下昨夜才想起自己身在何处。
起了身,一拉窗帘,哎哟要命!比昨天还不像话,日头当空,恐怕十一点都绰绰有余。她大叹了一口气,伸手放纵自己仰天一倒,“啪”一声摔在床上,又被床垫弹了一弹,才陷进被子里。
墙上的挂钟显示已然过了十一点,上午的课是赶不上了,出去吃碗面条然后去学校吧。问问汪老师寝室的事怎么样了,要是真的没有空出来的,就只能回亭子间再住两天了,但鱼龙混杂的,总觉得自己一个人住有点害怕,哎算了算了,忍忍就过了,能有什么事啊,瞎操心啥啊……江雁宁这样想着,从床上翻坐起来,拉直被子去洗漱。
要去上学,这一身冒充留学生的衣服是不能再穿了,还是得换上校服。江雁宁边这样想边在屋里找她那个装衣服的提包,结果寻了一圈才不得不接受“落在齐知礼车上了”这个事实。
1941年12月5日下午 12点15分
大同大学。
江雁宁走近理学院办公室门口,凑着头在门口看了看。今时不比昨日,在学校一堆老同学面前穿成这样可怪别扭的,她不自在地拉了拉衣摆,瞧见其他老师都不在,只有汪老师坐在办公桌前。
江雁宁甫一进去,还没开口,汪品夫倒先说了:“回来了啊,江雁宁。”
“嗯。”江雁宁点点头。
汪品夫打量了她一下,不由笑:“这一身知礼挑的吧,还真是他一贯的审美。”
汪品夫说得倒也很随意,只是江雁宁忽然听出点言外之意来:什么叫“还真是他的一贯审美”,这个“一贯”是什么意思?莫非……呸!这个不要脸的纨绔子弟——不不,明明是因为怕我出火车站被认出来才买的——可拉倒吧,他自己都说是为了虚荣心了——那不是心里话,还不是怕自己不好意思……
汪品夫看出她走神,干咳了一声:“江雁宁啊,是这样,寝室是暂时没有了。”
“啊?”她发起愁来。
汪品夫又说:“不过你不用担心,我那间寝室你可以先搬去睡。就是单人间恐怕没有那么热闹。”
“那您……”
“我晚上都是回家住的,寝室不过用来午睡。”
“感觉好像不太好,太麻烦汪老师了。”
“没什么的,反正今年也没几天了,等过了元旦再开学,学校会把寝室再分一分,到时候你就能和其他同学住到一起了——你东西呢?今天就可以搬过来了。”
“我放在严婉玲寝室里了,等一下去拿就可以,谢谢汪老师费心。”
汪品夫朝她笑笑:“那好,***室吧。”
江雁宁不走:“汪老师……”
“怎么了?”
她有点尴尬:“我课本和校服都落在齐知礼车上了,我不知道怎么联系他。您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她扯出一点堪称厚颜无耻的笑。
汪品夫摇头笑:“你这个马大哈哟!”他拨电话到齐家,接电话的是秀春,“你们少爷在家吗?”
秀春一听是他,声音里忍着的哭腔全泄出来了:“汪先生,出事体了!”
1941年12月5日下午 12点20分
银河街,江家。
董心兰气得把手里的抹布狠狠一扔:“你倒人格高贵!丑人样样我来做是吧!布施老朋友就算了,连升职都不肯和老同事去争,多少清高呀!也不想想家里柴米油盐哪样不要钱,我日日精打细算,落得一副蝇营狗苟的腔调,你倒还不食人间烟火了还!”
江志高坐在桌前,嘟囔了一声:“你看你,说这些做啥……”
“我叫你去和齐家人说,只要齐知廉肯明明白白调查凤平的事,还凤平一个清白,我们江家第一个搬出银河街,你怎么就不肯了!怎么就没义气没道义了!”
“你叫我怎么开得了口!李家妈要等着国梁回来,老吴腿不能走路,沈家又是那么一大家子……说我们第一个搬还不等于当了叛徒了。”
“那你有本事不要从上海搬回来了啊,不是落得个清净嘛!”
“有啥办法啦,报馆里工资又不涨……”
董心兰越说越气:“你也知道啊!我当年也是正正经经读了书的,洋行里打字员做得蛮好,你非要跟我求婚,说什么给我幸福人生。全是狗屁!这二十多年来都是我在操持这个家,当年早知这样,我就该安安心心做个打字员,结什么狗屁婚!”
江志高大气都不敢出。
董心兰还在慷慨陈词:“要讲义气讲道义?好啊!这银河街的房子是谁的!谁家的地契房契?占了人家的东西不还倒还义薄云天了!”她冷笑了一声,“好啊,你不去可以,我去!凤平是我的儿子,只要他没错,我就一定支持到底!”言罢大步跨出门去。
江志高急了,快步追上去:“心兰心兰!”他拦住自己太太,“你说得不错,我去。”
谭为鸣开着车到了银河街。
这回与往日不同,车里还下来四个壮汉,穿着黑衣,剃着光头,一看就怪瘆人的,更别提还背着手来来回回在街上走了。
江志高也顾不得打量这些壮汉了,见谭为鸣走到自家门口便招呼他:“谭先生,进来喝杯茶。”几日间来,彼此已经有一些熟识。
“不了,江先生客气。”
“进来喝一杯吧,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讲。”
1941年12月5日下午 12点25分
“少爷让人给挟持了!”
汪品夫心脏猛跳:“在哪?”
秀春哽咽着说:“松、松江纺织二厂,老、老爷刚、刚去。”
汪品夫放下电话,脑中某根唯恐天下不乱的神经开始“蹦蹦蹦”地跳,他搓了搓脸,站起来叹了口气:“江雁宁,你先***室去。”
江雁宁有种不太好的预感:“怎么了?”
汪品夫看了她一眼,面前的人眼中有真实的关切,他犹豫了一下,据实以告:“知礼被人挟持了。”
江雁宁愣了一下:“什么?”话出了口才算反应过来,“怎么办?我们快去!”脸已经白了。
汪品夫住得不远,往常多数是走路上班,这回要赶去松江,只能先拨了电话给家里,让他们派车来接。
1941年12月5日下午 13点50分
松江,齐氏纺织二厂。
二楼阳台上,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用手里的尖刀对着齐知礼的喉头,他身上那件棉坎肩打满了补丁,两只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楼下。
汪品夫急得跳脚,问旁边围观的工人:“怎么回事?”
“少爷中午刚到厂子里,这个神经病就冲进来,提两桶火油一通乱倒,我们吓得全部跑出来,他上去拿刀对牢少爷,喏,现在就这样了。”
旁边的工人插嘴:“这神经病瘦成这腔调,本来么我们几个人上去早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了。现在没办法,他倒了火油,嘴里还衔着烟,一不小心就要出大事的。”
汪品夫长叹了一口气:“他为啥要到这里来?”
齐树新看见他,近前来:“贤侄。”他两个眼袋硕大,脸上全无血色,月余未见,汪品夫觉得这位一贯气势十足的长辈猛然老了二十岁。
“齐伯父。”他也不虚客套,“这是怎么回事?”
齐树新叹了一口气。
江雁宁却已明了一切,自打看清那个持刀的男人的脸后,来龙去脉都霎时清晰了,歉意与羞耻感奔腾着涌上心头。
齐树新苦笑了一声:“知慧的事你是知道的,银河街要收回来转手,喏,这就是知礼爷爷一心要护的银河街老街坊。”这时有个手下跑来,低声说了句什么“警察”之类。
江雁宁顾不得去听,她记挂着齐父的话,侧过头去问:“汪老师,齐老板说的‘知慧’的事是什么事?”
“知礼的姐姐让人绑架了,对方敲诈一大笔赎金。”
江雁宁愣了一下:“所以才要收回银河街变卖吗?”
汪品夫仰头盯着阳台,深深地叹了口气:“是啊,齐家最近真是焦头烂额。”他想必并不知道银河街是江家祖宅所在。
江雁宁舌桥不下,当下难以描述心情,遑论对齐知礼那点日益浅淡的怨恨了,此刻更是已土崩瓦解。全然理解了这些天来齐知礼的焦灼、忧虑,甚至不近人情——“他心里该多担心呀!而我还……”江雁宁这样想的时候,心里一阵酸楚。
她抬头看阳台上的齐知礼,他被尖刀顶住喉咙,脸色煞煞白,显然是紧张的,但却面无表情,始终在强装镇定,可见理智压住恐惧占了上风。
齐树新决定再和挟持者谈一谈,扯着嗓子朝楼上喊:“王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在租界给你找个公寓,你现在下来,我马上让人带你去看。”
“呸!”王七贵一口唾沫下来,围观群众纷纷避闪,“带我去看?我半路让你们弄死都没人知道!”
“王先生多虑。在场诸位都可替我齐树新做见证,我保证将你安全送达。”
“你少在那说得好听!‘安全送达’,送达以后呢?日后的事情怎么说得清!”
齐知礼被他手里那把利刃逼得脖子后仰,听到这里动了一下喉结,试图说服王七贵:“王先生,这你大可放心,家父既然应下……”
“你闭嘴!”王七贵目眦尽裂,手里刀刃一翻,即刻在齐知礼脖子上划出一道血痕,“‘应下’?你们齐家应下的事还少吗?当年说好的银河街永租权呢?还不是说废就废,说翻脸就翻脸!你们齐家说话还不如放屁!”
齐知礼的惊惧比刺痛来得更快,刀口划破皮肤的时候,他脑海中除了“我不能死”外一片空白。齐树新在楼下看得心都要扑出来,怕王七贵再做出什么疯狂举动来,除了喋喋的“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再不敢多讲。
江雁宁目睹这刹那,只觉背上的汗毛根根立起,一种巨大的惊惧淹没了她——“齐知礼不能有事!”当下只余这个念头。
“七伯!”嘴快过脑,等江雁宁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的时候,话已出了口——但她甚至有点庆幸自己的冲动。
王七贵这才看到她:“你怎么在这里?”他并没有放松警惕的意思。
“我能不能上来说?”她举手作投降状。
王七贵看着她,没有应允,但也没有制止。
这是在场无人想到的转变,江雁宁一时吸住所有目光。
汪品夫伸手拉住她:“江雁宁……”
齐树新走过来,上下打量着她:“姑娘,你是王先生的?”
“街坊。”江雁宁看着他,“齐老板,我是银河街住户。”
莫说齐树新,连汪品夫也一惊。
江雁宁看出他的忌惮:“齐老板放心,令公子曾帮过我,我绝不会置他安危不顾。”
齐树新隐约松弛了一些:“但是眼下恐怕不太适合上去,太危险了。不如再等一下……”他把警察要来的话咽了下去。
江雁宁竭力挤出一个微笑,没有再说什么,快步跑进车间上了楼。
王七贵还是一手拿刀,一手握着旱烟杆,时不时凑上去吸一口。是以无人敢动他,地上的火油沾湿了鞋,王七贵手里的烟杆要是一掉,整个车间即刻沦为火海。
江雁宁站到阳台上,王七贵侧着身看了她一眼,不悦道:“你来干什么?”
江雁宁力图冷静:“来看七伯。”
齐知礼面向楼下,此刻正背对着她,刀刃在前,他无法回头,声音里却有一股怒气:“江雁宁,你下去!”
江雁宁置若罔闻,对着王七贵:“七伯,两天前我差点落在日本人手里,是他救了我。”她指着齐知礼,“知恩不报枉为人,今日我不能眼睁睁看他这个样子。”
王七贵气坏了:“雁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银河街一拆那可就连老窝都没了,是住到桥洞还是乱葬岗去?哦对。”他冷笑一声,“你家不缺地方住。”
“我听刚才齐老板说……”
王七贵不耐烦了:“你哪凉快哪待着去,我没工夫听你说这些!”
“我不会走的。”江雁宁看着他,倒是出乎意料的坚定,“七伯,我来换他。你让他下去,我留在这里陪你……”她狠了狠心说,“陪到他们不拆银河街为止!”
“你一个小屁孩算什么东西!”王七贵嗤笑一声,“莫说我一个,就是我俩一起烧死在这里齐家也未必抬抬眼皮。”
“那可不一定。”江雁宁站着深吸了一口气,凑到王七贵耳边,压低声音说了句什么。
“什么?”王七贵惊得叫起来,“你怀了他的孩子!”
江雁宁没想到他还要重复一遍,一张脸刹时涨得血血红,撇过头连齐知礼的背影都不敢看了,最好哪里有地洞先让她钻一钻。
王七贵咂嘴:“小丫头片子看不出啊,本事倒还真有一点,攀上齐家将来可就吃香喝辣了吧。”
话都赶到这份上了,江雁宁也顾不得脸皮了:“所以七伯你看,他刚才一见我上来多着急……”
齐知礼震怒,又无法发作,气得咬牙切齿:“江雁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是不是疯了,为了换自己安全什么话都讲得出口,连名声都不要了。楼下还好,距离远风又大,未必听得清,可是王七贵住得离她家那样近,往后要是把今天的话传出去,她以后怎么做人自己没想过吗?
江雁宁由他讲去,只顾和王七贵说话:“七伯,咱们要的也不过就是保住银河街,万一真的今天交待在这里,银河街保住又有什么用呢。我有个办法,您放齐知礼下去,我保证他们不敢动银河街。”
“我凭什么信你?”
“凭我带着齐家的孩子留在这里,要是事不成,我身上两条命交给您!”
王七贵将信将疑地看着她。
齐知礼气得几乎吐血:“王先生,您不要听她胡说八道!我和她不过是前两天刚认识的泛泛之交——江雁宁你还不快滚!”
江雁宁再笃定没有:“七伯你看他!泛泛之交会自己不想逃命非要我走吗?还不是担心他的宝贝孩子。”
王七贵一想觉得很有道理:可不是嘛!要是真的像陌生人一样,那换谁不得自己先逃!接受“事实”后,他一把扯住江雁宁,踹开齐知礼,把刀架在江雁宁脖子上,狞笑道:“齐少爷,我手里现在两条命,你下去好好想想,银河街这事到底该怎么办。”
齐知礼重获自由,但紧绷的神经丝毫没有放松,瞪着江雁宁,恼怒已是极细小的部分了,忧虑却急剧放大。
江雁宁不敢直视对方,王七贵对她尚算手下留情,刀搁得远了点,这甚至给了江雁宁撇头躲过齐知礼目光的机会,她嘟囔一声:“你还不快走!”
“我不走——王先生,不如我们……”
江雁宁喝断他:“废话少说!让你下去就下去,和你爹好好想想到底要不要答应七伯的要求!”
齐知礼犹疑了一下,终于说:“好。”他倒退着走出阳台,咯噔咯噔地下了楼。
楼下,齐树新看见儿子出来,老泪纵横:“医生!医生呢!快帮知礼包扎一下。”
齐知礼这才感受到脖子上一阵火辣辣的疼,伸手摸了一下,掌心一片殷红,饶是如此,仍然制止上前来的医生:“父亲,我们先谈一谈。”
父子俩站在围墙下,冬日的阳光在风里显得格外单薄飘忽。
齐知礼率先开了口:“父亲,我们眼下住的房子抵押出去值多少?”
齐树新看着他:“怎么,不想收银河街了?”
齐知礼搓了搓脸:“我只是想……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筹钱,毕竟银河街真的……那些街坊也真的不容易。”今日王七贵这等行为他当然难以原谅,恩将仇报算什么东西!哪堪为人!但他又想起谭为鸣说的家徒四壁却到街口买二两卤肉请他吃饭的祖孙俩,更何况……更何况今日侠肝义胆的江雁宁……
齐树新说:“那姑娘呢,还在上面?”
“嗯。”
“她怎么就巴巴地往火油里跑,还轻轻松松把你换下来了?”齐树新瞪着儿子,“你眼下已经是这个念头了,可见今日这场戏做得真真像样——这姑娘就是银河街的,你可知道?”
齐知礼点头:“知道。”
齐树新不可置信:“知道你还心软?你想什么呢!”他冷笑一声,“银河街两个刁民本事真是可以,把我儿子噱得五迷三道。”
“父亲,不瞒你说。这姑娘书香门第出生,一家亲厚,是父母掌上明珠,断然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戏。”
齐树新睨他一眼:“那可未必。”
齐知礼深呼吸一口,据实以告:“如果我说,这姑娘几天来一直跟我在一起呢?”
那边厢,江雁宁正展开心理攻势:“七伯,咱们两家什么关系您是有数的,你们家根宝还是我妈奶大的。我肯定是和您一条心的,银河街收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当然有了,还不是全留给你肚里那个。”
“咳。”江雁宁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她都忘了这茬了,可惜自己撒的谎含着泪也要圆下去,“收了回去还不是卖掉,谁晓得钱到哪里去。退一万步讲,就算钱老头藏着,可齐知礼还有个姐姐呢,老头可宝贝她了,工厂的事楼下工人不都说了,往常一向都是她管的,她能让钱落到我手里来?我们齐家自己住着就不一样了,她敢来收?咱们银河街一众老街坊住在一起开开心心,我做啥要给齐知礼他姐姐铺路,我又不傻。”
王七贵松了口:“那你说,怎么才能把银河街留住!”但手并不松,仍然架在江雁宁脖子上。
江雁宁不躲也不求饶,任由刀这么架着,想了想说:“七伯,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下他们来了,我们先听听他们怎么说,银河街的事肯不肯就这么算了,要是行的话,咱俩就下楼去……犯不上鱼死网破,根宝小小还有七婶都在等着您回去呢。”江雁宁心里七上八下,王七贵这人银河街哪个不知,出了名的坏脾气,一言不合就真刀真枪地上,无人敢惹。
“那要是他们说话不算话呢!”
说话间齐家父子走过来,仍然是齐树新开的口:“王先生,经过我与犬子再三商议,决定银河街不拆了。您快下来吧,回去安安生生地住着。”
王七贵又伸出手里的烟杆嘬一口,咪着眼睛说:“你们拿什么保证?”
“在场诸位都可与我齐树新做个见证,今日我在此说的话句句当真,绝不食言。”
说话间厂区门口一阵骚动,一队警察蹬蹬蹬地跑进来,腰上还别着枪套。
王七贵大怒:“***!还想找人来毙老子!”他猛吸一口烟……
坏了!江雁宁余光一瞥就知道要出事,她猛一转身一手盖住烟杆口,“七伯七伯,求求你,我还不想死!”她这回是深切感受到濒死的恐惧,情难自已,已经带着哭腔。手上阵阵剧痛传来,皮肉似乎都在高温下滋滋作响。别人不晓得,银河街的人却哪个不知,王七贵一说脏话就是要拼命了,对方只有即刻认怂的份。
齐知礼心脏简直要蹦出来,也顾不得礼仪了,手一挥把一众警察挡住,眼睛血红:“出去!”
几个警察哪里料到他这种态度,脸上僵了僵,碍于齐树新面子才没有骂骂咧咧,冷着脸走了。
王七贵神色细微地缓了点,江雁宁小心翼翼松开手,试探着说:“七伯,他们也保证过了。您要是还不放心,不如这样,吓一吓他们,就说他们要是说话不算话,我们银河街人各个都来找他们算账,包管让他们生意做不下去。”
王七贵沉思了一下:“那就照你说的办。要是他们说话不算话,我第一个找你们江家人!”
“是,您放心。”放心个屁!要是能活着出去,明天就回去让爸妈带上奶奶搬家!
他冲楼下喊:“那就再信你们一次!要是再来收街,我包管把你们几个厂烧得一干二净!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那就是银河街的弟兄一起来烧了!你们不相信尽管来试试!”
齐树新赔笑:“绝不会再来,王先生大可放心。”
又纠缠着哄了好一会儿,王七贵才大爷似的下了楼,烟袋杆还握在手里,以表随时仍可同归于尽的决心。
齐树新差司机:“小李,送一送王先生。”
王七贵手一挥:“别别,齐老板,你们的车我可不敢坐。”
齐知礼记挂立在一旁的江雁宁,没有功夫再听父亲应付此等狂徒,抽出两百块来:“那劳烦王先生自己叫辆车走吧。”
王七贵目的已达到,也晓得下了楼不再占上风,接了钱拿手指着齐知礼:“说话算话啊小少爷。”头也不回地走了。
江雁宁坐在树下呲牙咧嘴,汪品夫正陪着医生处理她手上的烫伤。
齐知礼疾步过去看,江雁宁那只原本细白的手此刻又红又肿,血肉模糊,成串的水泡惨不忍睹。齐知礼倒吸一口凉气,蹲下来看着江雁宁,轻声问他:“痛不痛?”
江雁宁笑眯眯地看着他:“不痛——咝……”
齐知礼万万没想到她会这样回答,他本以为江雁宁是会呛自己的,结果她居然忍着一脸的“哎哟喂痛死我了”说不痛——是安慰自己吧,怕他有心理负担。
齐知礼站起身来,没有说什么。立在院子的冬青树旁,看着江雁宁,悠悠地做了个深呼吸。
厂里要彻底清一清干净,齐树新给工人放了一天假,叫来齐知礼:“这两天你就别出门了。等一下我去银行,银河街卖么暂时先不卖了,拿过去抵押,先凑一凑也能将就。”
齐知礼正要说话,齐树新抢过他话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了。齐家在,银河街才可能在。若是将来真有个三长两短,抵押的东西收不回来,银河街何去何从也不是我的能力范围了。”
齐知礼知道父亲说得一点错处都没有,但有一点:“抵押的钱又没有卖出去多,缺口哪里补?”
齐树新瞪着他:“能怎么办!如你所说,家里的宅子也押出去呀!这下要是再遇上点周转麻烦,好了,乡下买块地种番薯去吧!”
齐知礼知道父亲这句听着像气话,但也未必是耸人听闻,阿姐的事连自己都忧得心神不宁,何况父亲?他不止要操心阿姐,生意上一如既往有大堆事,瓷器商据说也上门来讨过几次债了,饶是这样,人前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恐怕一根弦已快绷到极致。他不知该如何安慰父亲,只能轻轻拍了拍父亲的背。
齐树新没有再谈下去,只说:“走吧,我还要回办公室,你让小李送你回家。”
“您先走吧父亲,我搭品夫的车回去,路上还有点事要跟他谈一谈。”
1941年12月5日下午 15点50分
汪家的车上。
司机和汪品夫坐在前面,后面坐着齐知礼和江雁宁,两个人各自倚在边上,隔得远远的。
齐知礼开了口:“你说你傻不傻,冲上来干什么,被人拿刀顶着很有趣啊?要是真打起来你一个小姑娘家家怎么是他对手。”
江雁宁嗤笑他:“好像你是他对手一样。还打起来?你倒是有机会打啊!你看到他拿烟杆的那只手的小指没?”
齐知礼不解:“没。怎么?”
“你当然没看见啦,因为他根本没有左手小指。”江雁宁做了个“咔嚓”的手势,“那是他和七婶吵架自己剁了的。打起来?你想得倒美,他一把火说放就能放。”
齐知礼盯着她,死死盯着她,最后却只是说:“所以你是真的傻。”又补一句,“又笨又傻。”
“我笨?你问问汪老师。”江雁宁叫汪品夫,“汪老师,你告诉他我笨不笨!”
汪品夫忽然打了声呼噜。
齐知礼“噗嗤”一声笑出来,拍他肩膀:“好兄弟!”又对江雁宁说,“回去记得换药,每天一次。”
“知道了。”
“别忘记啊!还有脖子上的擦伤,也要注意……”
“哎呀,都说知道了!”
连汪品夫都听不下去:“行了行了,你放宽心,我会盯着她每天去校医室的。”
“那就好——哎对了,品夫,她的寝室安排得怎么样了?”
汪品夫本正闲散地靠在椅背上假寐,齐知礼这一问,他忽然坐直了回过头来看,用一种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光审视着好友:“你倒什么都很清楚——我那间单人寝先给江雁宁住,等明年排寝室再调动。”
“费心了。”齐知礼又拍了拍他肩。
汪品夫忍笑挑了一下眉:“好,你就当我费心了吧。”
江雁宁见他们停了对话,便问齐知礼:“那七伯呢,你们会不会叫警察把他逮起来?”
齐知礼斜睨她:“你还操心他哪。”
“替七婶操心。”
“他不是自己都说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银河街的弟兄要一起来找我们算账嘛,我哪里还敢叫警察抓他。”
江雁宁扯着嘴角尴尬地笑了一声:“这句话是我教他说的。银河街……七伯在银河街没什么弟兄。”
“所以这是让我找他秋后算账的意思吗?”
“不是。但是……”
“嗯?”
“我怕他再来找你。”
齐知礼心里像淌过一条飘着花瓣的春日的小溪,他忍不住伸手抚了抚江雁宁的脑袋:“放心吧,不会来了,银河街真的不拆。”
“啊?刚才不是骗他的哦!真的不拆啦!”江雁宁一下子开心起来。
“嗯。”齐知礼看着她,嘴角露出一点细小却欣慰的笑意。
江雁宁却猛地想起那句“知慧的事”,她侧过头去靠在车窗上,扬起的唇角骤然垂了下来。
1941年12月5日下午 17点30分
大同大学门口。
放江雁宁下了车,汪品夫本要请司机送齐知礼回家,结果发现谭为鸣正开着车迎面驶来。
齐知礼同好友道了谢坐上自家的车。
甫一上车,就听谭为鸣讲:“我听小李说您坐汪少爷的车回来,就过来看一看——没受伤吧?”
齐知礼松开衬衫领口,深深吸了两口气:“没有。”
“银河街不拆了?”
“嗯。”
“那钱呢,钱哪里来?”
齐知礼苦笑了一声:“能押的都押了呗,还能怎么办?”
“都押了?这么大动作,恐怕风声没几天就要传出去,说齐家产业风雨飘摇了。”
“就当是饮鸩止渴好了,哪还能顾那么多。”
“本来我还有件事要跟您讲,现在看来,也没有必要了。”
齐知礼随口问:“怎么说?”
“银河街江家——就是泼辣小姑娘那家,本来她父母倒是肯第一个搬。”
齐知礼坐直了:“哦?”
“还不是有条件的。他家儿子在当兵,犯了点军纪,照江家太太说是救人误了时间,不算是大错。听说罚了她儿子降级的正是知廉少爷,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了两家的关系,非要找我们说这个情。”
“江家还有个儿子?”
“是。叫什么来着……对了!江凤平。”
“你怎么跟他们说的。”
“我哪敢应啊!知廉少爷您是知道的,那个刚正不阿的脾气哟,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齐知礼点点头:“行,我知道了。”
1941年12月5日晚 18点05分
齐宅。
趁着齐父还没有回来,齐知礼拨了个电话个堂兄齐知廉。
对方开口先问:“知慧的事怎么样了?”
齐知礼心情落到谷底:“毫无头绪。”
“你多照顾二叔,如今他毕竟也上了年纪,身体是首位,不能知慧的事还没解决你们先垮了。”
“是是。”
“钱的事呢……”
齐知礼打断他:“哥,我有事要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
“今天二厂有人闹事,往车间浇了一大桶火油,还挟持了我,我差点就……”
齐知廉一贯冷静,饶是如此也深吸了一口气:“没受伤吧?”
“小事,一点皮肉伤——是个姑娘救了我。”
齐知廉好整以暇:“所以要请我帮的忙和姑娘是什么关系?”
齐知礼讪笑一声:“知弟莫若兄。这姑娘的哥哥叫江凤平,听说哥您罚了他降级?”
齐知廉冷下声来:“齐知礼,你知道的,我不吃这套。”
“哎呀,哥你看你,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你就不给我好脸色了。”齐知礼拿出小时候以小卖萌的那套,“听说江凤平是为了救人还是什么来着?”
“我不问原因,我只看结果。”
“哎哟,你问一问!你看在人家妹妹舍身救你弟的份上,你问一问!”齐知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没让参谋长大人您徇私枉法,就让您查一查,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要是实在罪不容赦,我保证一句话也不多讲,行不行?”
“下不为例啊!”
“谢谢哥!我就知道你最通情达理了!”
“少来这套!”齐知廉隔着话筒都想瞪堂弟一眼。
有什么办法呢,大哥不易做啊!